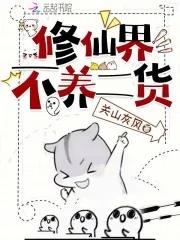小說門>煮蛇姑娘免費閱讀 > 第158頁(第1頁)
第158頁(第1頁)
但阿祖還一直不肯睜開眼睛,他就用小棍子将他眼睛撐起來。
阿祖的眼睛已經瞎了,撐起來也不會動。
更糟糕的是,他不會呼吸,即使煙塵落在他臉上他也不會再打噴嚏,而他身體也變得冷冰冰起來。
白伶榇想,阿祖應該還沒死,因為他還在這裡,肉還在,骨頭也在。
日月山下,九月就開始吹起了寒風,他覺得阿祖是冷壞了,就像有一年挂白毛風的冬天,回來的時候手腳全身都不能動了,他于是費盡全力,用那把唐刀将剩下的棺材劈了,拖過來,一點一點燒,棺材裡面有陳年的血,積累的油,燒起來哔哔啵啵又香又甜,整整一晚,讓人一口又一口的咽口水。
他燒光最後一個棺材闆的時候,意外看到了他娘~親留下來的東西,幹涸的骨架是緊緊包~裹的皮囊,旁邊是碎裂的蛋殼,或許是蛇的蛋,或許是别的。但最重要的是上面的一封信。他坐在火堆旁反複看完了那寥寥數筆的信。
他的父親姓白,原是江南的一個赤腳大夫,在戍邊時候,因為救了将軍得了賞識,封了個小官,發了筆小财,後來買了被貶斥的犯官女兒為女寵。信寫得倉促潦草,最後寫了他父親的祖籍,想來是他母親慌亂中留下的,想着有一天他能帶着去找到父親。
白伶榇看完信,轉頭就看到阿祖的眼珠子掉了下來,啪叽一聲摔破在地上,阿祖的喉嚨因為灌了太多熱水,現在已經發紫,又因為溫暖的火,即使在寒冬,渾身也有了一股說不出的味道。
所以,這就是死麼,那死真是一件讓人糟心惡心的事情。
白伶榇花了三個月時間,以讓人想象不到的毅力從幹涸的戈壁和沒有盡頭的草原走了出來。以前沒有人和他說話,他常常覺得寂寞,現在他看到了數不清的人,卻覺得更加寂寞。
有些死的,有些活的。
他終于知道為什麼阿祖守着義莊,卻一個人都不肯拖出去埋。
埋在泥裡的人,埋得深了,老鼠會來,埋得淺了,野狗會刨出來。
這世道,人和人的差别隻在于活的人聞着新鮮。死的人聞着惡心。
白伶榇到了白員外的祖籍永州,依附藩鎮,他的日子過得還算不錯,新的嬌妾又添新子新女兒,半個院落都是莺莺燕燕的聲音,哪裡還記得多少年前那個在馬車被推下來的犯官之女,更逞論那個不知出路的兒子。
他去過一趟,連側門都沒進去,守門的仆人一腳将他踢開。
“像你這樣來認爹的,一年沒有十個也有八個?我們員外的小姐公子這麼多,哪裡要你這樣一個叫花子?滾滾滾。”
他又問,能不能給他一個饅頭。
那仆人嗤笑:“你要是叫我一聲爹,我給你一個。”
七歲多的白伶榇睜着黑漆漆的眼珠子:“爹。”
那仆人哈哈大笑,又一腳踢開:“你要是個姑娘,給你一個饅頭不算什麼?你一個大小子怎麼這麼沒出息,有奶就是娘呢?”
另一個年紀小點的過路丫鬟看不過去,罵那門童:“小司兒你何苦欺負一個孩子。”又給了他半塊吃剩的饅頭。
叫小司兒的仆人笑:“左右阿香姐姐你是要上老爺房的貴人姐姐,小司兒這廂有力了。”
白員外獨好美色,家中嬌妾無數,略微平頭正臉的丫鬟也不放過,他的大娘子又是個心狠之人,管不住自己相公,就将氣撒在這些弱女子身上,一旦新鮮感不在了,逞論大人,甚至連這些姬妾生的小孩也悄悄處理了好幾個。
白伶榇于是在永州住下,他生得好,認識字,做事情心狠手辣又講道理,不過幾年附近的小乞兒都喜歡跟着他混。
他那時候便開始挑選裡面生得好的,教她們認字說話、婀娜舉止。
然後将這些姑娘一一舉薦送出,得了第一筆錢,接着是第二筆,第三筆。
如此不過幾年,白伶榇便進了顧家的門。
那日~他穿戴整齊,星眉劍目,唇紅齒白,翩翩公子一般,看癡了顧家屏風後多少丫鬟小姐。
白員外坐在花廳等他。
白伶榇還特意帶了從域外風幹肉這樣的特産奉上。
白員外新得了嬌妾,又吃了這美味,對白伶榇贊不絕口。
此肉品質其佳,說不出的口感,吃了便上瘾,一日不食,當真如抓心撓肝一般。
一旦吃了,通體舒暢,更妙的是,在床~上更是英姿勃發。
白員外便愈發欲罷不能,加之之前他用了此肉孝敬上官,上官緊催,他無法,隻好頻頻來見白伶榇。
白伶榇初時給得爽快,漸漸也有為難之色,價格更是一路水漲船高,而那白員外的上官為了前途又将此等好物孝敬了自己那年近七十的恩師,讓恩師再次一展雄風。
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
相鄰推薦:我用最傻的方式愛過你 暴雨末世,我打造三層樓安全屋 一葉知秋 給你愛情這把刀 聽風熱吻我 1003 系統,你确定嗎 月色琉璃 愛上足療女 絕愛無期 雜貨店 如果愛情不回頭 誰說思念無聲 我靠學習變美[系統] 切膚之痛 漠沫不得語 海賊:快樂尋寶,伊姆對寶箱過敏 煙火裡的塵埃 overlord:洛爾斯達聖君 情似毒藥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