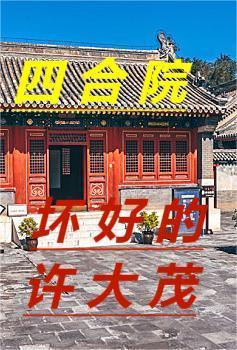小說門>想做你的白月光劇透 > 第32頁(第1頁)
第32頁(第1頁)
霍司容将熱騰騰的肉包扔進林襄懷裡,林襄看也沒看,一把扔出窗外,掀起被子躺下睡覺。
霍司容額頭繃出青筋,素來說一不二的霸道性格又一次慘遭挑釁,頓時怒發沖冠,大手捉住林襄細瘦的小胳膊,一把扯出被窩,掐着他沉聲說:“你未免太放肆了。”
林襄擡起下颌,輕蔑道:“怎麼,霍先生還沒結婚就想家暴嗎?”
霍司容有片刻怔忪,手心拽着的人輕飄飄沒幾分重量,眼尾稍稍挑着,斜過來觑視他,那神情中簡直充滿了不屑和煩躁。
林襄還喜歡他嗎?霍司容不由自主地想,他迫切想知道答案,但面前崇慕他許久的孩子,卻不再用從前那般赤誠的目光注視他。
眼前的林襄,陌生到霍司容快要不認識,奇怪的酸澀在憤怒熄滅後湧上心頭,随之而起的是各種各樣的不甘和不可置信,他無法判斷百味陳雜的情緒後究竟是哪種感情作祟,又是誰的心蠢蠢欲動。
“或許……”霍司容自言自語地冒出一句:“我應該對你好點。”
——“你就對我好點呗。”那一年林襄在他身下,在四無邊際鑲金綴玉的大床上,認真地好像在填塗他的高考答卷。
他把所有的回答交給霍司容,等候對方無所顧忌的評分。
這句話就像阿裡巴巴對神燈吹出暗号,拉扯着林襄自年少起便躁動不甘的心。
他凝視着霍司容,十年過去,這個男人一如記憶中那般高大,站在他們家的小破窗前,遮住了所有的陽光,從此眼裡隻有他逆光的身影。
瞬間心灰意冷,連脾氣都發不出,軟着四肢任由霍司容牽扯,一雙眼睛越過他望向蒼白的天花闆,苦笑陣陣:“先生,您何曾為我而來?現在說這些,為時已晚。”
“如果亡羊補牢、懸崖勒馬呢?”
“分桃者色衰愛弛,斷袖者飲鸩絕命,先生的心,林二要不起。”
兩個人一上一下,對視彼此。
十年光陰倉促,三年隻餘糾葛,原來從頭到尾,林襄一味的付出就未嘗奢望回報,隻是霍司容太狠,生生砸痛了少年不求回報的大心髒。
“被撕的那份授權書是複印件,”霍司容蓦然道,“原件在家裡保險櫃中鎖着。”
林襄眼前一亮,很快又黯淡下來,嗤笑一聲:“是嗎?您又不可能給我。”
“等結了婚……”霍司容低頭,咬了他的耳朵尖,熱氣氤氲暧昧,低啞性感的嗓音鋪就一條引人遐想萬千的前路,他就像在展望他們的婚姻,盡管林襄明白這有多麼虛假,卻不可避免被他勾住心神:“什麼?”
“都是你的。”霍司容說。
林襄呆住了。
霍司容在他身旁坐下,兩隻寬闊溫熱的手掌包住林襄雙爪揉搓,漫不經心地說:“胖了好看些,你過于清瘦,我讓你吃東西,并非害你。”
林襄眨了眨眼睛,難以抑制地動容:“我知道您在騙我,哄着我給哥哥捐血,但是……”
三年了,您稍微念一句情話,我便願效飛蛾撲火,此後若粉身碎骨,亦能大言不慚道為愛殉身。
上大學後的兩年,霍司容待林硯有多周到,林襄一一看在眼底,從前沒有時便不奢想,後來和霍司容滾了床單,縱容對方各種無理要求,心想着,霍先生會否有那麼微末的偏愛,像天上掉餡餅,落到他林二頭上。
不看功勞,也有苦勞啊。畢竟陪在霍司容身邊,了解他至深的人,是林襄而非林硯,不是嗎?
“哥哥二十三歲生日那年,你帶他遊了一圈歐洲,哥哥滿二十四,你買了紐約、東京、首爾、巴黎和倫敦的大屏廣告,慶祝他過生。”林襄耷拉肩膀,眼眶微澀,低低地說:“能不能,等我二十三的時候,您跟我說一句……”
“說什麼?”霍司容好奇地看他,林襄擡起腦袋,彎着眼角笑了笑:“說,你來啦,我等你好久了。”
霍司容陷入沉默。
林襄推開他的雙手,拉起柔軟被單蓋回自己身上,怅然喟歎:“隻可惜,木已成舟。”
霍司容和林襄打了半天的啞謎,終究搞不懂他們滿肚子墨水的人,心裡都裝着多少疙瘩,于是關了室内燈光,合緊厚重的遮光窗簾,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裡,靜坐整夜。
翌日大清早,霍司容在六點依靠生物鐘準時醒來,林襄嗜睡,這會兒沒醒,他輕手輕腳出了門。
聞堯正百無聊賴立在門外,雙手插兜,抖腿等候。
霍司容面無表情地出現,聞堯聳了聳肩膀:“哄好了?”
“畢竟是個孩子。”霍司容不鹹不淡道,臉上一如既往無甚表情,仿佛昨晚片刻溫情不過假象,他依舊是那位六親不認、心狠無情的霍先生。
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
相鄰推薦:當不成迷弟的我隻能出道了+番外 潔癖貴公子 恐怖小說之他說别回頭 月下仙子 流浪在中世紀做奴隸主 神豪,不一定必須做大生意 咒術師哪有不瘋的 夫夫外出取材中+番外 少奶奶又在外面訴苦了 穿越以後,我躲在幕後 穿越種田之農婦 快穿:炮灰白月光她不當了 巨龍養崽日常[西幻]+番外 瘋批男主養的乖寶寶在末世殺瘋了 渴望被愛的僵屍+番外 70年代極品婆婆+番外 軍婚:老大,嫂子又雙叒被人揍了 傻子 傻村夫的“傻”娘子+番外 冰山鶴融化了嗎